去似朝云无觅处 梦也何曾到谢桥(1)
去似朝云无觅处 梦也何曾到谢桥(1)
采桑子
—清•纳兰性德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
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
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我的老家是豫西的一个小山村。要说山村,其实有点不确切,我们县地处伏牛山余脉,海拔百来米,就地貌而言,就是连绵不绝的土包。土包和土包之间夹杂或长或短的沟沟岔岔,百来口的原住民村落像芝麻一样散落在这些土包上。

我们村很少有外姓,一律姓陈。据村里年长的同辈哥哥说,我们村里的陈姓是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杀人太多,从河北颍川迁居到此,族谱上有记载,我刚刚记事儿时同辈哥哥已经发白齿稀,好在我们比邻而居,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我家大门外的山墙朝阳处和村里的乡邻喷筐儿(豫西地方话,约等于现在的侃大山,特指闲聊)。很大一部分的历史常识、民间典故均来自于这位同辈老哥哥绘声绘色的神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善恶是非观的雏形基本渊源与这位博学多才的邻家大哥。
邻家大哥弟兄众多,(以后有时间可以单独写一篇有关于大哥的文章,在此不多赘述)其中有一位堪称奇人。因为排行老九,大号叫九芳,我们统称为九哥。
九哥是一个煤矿工人,在八十年代的农村人眼里,是吃公家饭的,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可拿,是令人羡慕嫉妒的人呢。
九哥会拉弦子,就是拉二胡,据说技艺超群,经常到县里的剧团客串演出。九哥长得人高马大,娶了个老婆也漂亮,唯一不足的就是生了两个姑娘,然后九嫂的肚皮就再也没有动静。于是九哥很忧伤,每天晚上的二胡拉的更加幽怨哀伤如泣如诉。
九哥还有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独有的绝技,每天都要骑着自己的一个把手的自行车去15公里外的矿区上班,九哥的自行车是他自己特意拿钢锯锯掉了一个把手,没有车铃,没有刹车,上坡全靠猛力蹬,下坡全靠一腔勇,九哥的自行车走到哪里随意扔在那里,从来没有人会去觊觎。大概是除了九哥,谁也吼不住这胯下之物吧,不单单是炫技,是无法成为九哥那样风一样的男子。

风一样的九哥,在矿上是个电工。不用下井,即便下井也是吊儿郎当的,平时就在地面上,和一堆老娘们儿打情骂俏,开一些荤到裤裆里的玩笑,然后一群人哈哈大笑。其实,九哥一点也不油腻,非常热心的一个人,尽管没有儿子,九嫂也没有被人歧视,经常和同龄的女人们在一起纳鞋底子,打那种四个人玩的升级,九嫂性子绵柔,九哥多情而豁达,非常互补的一家人。
一个秋雨绵绵的清晨,九哥休班在家,头一天夜里风雨交加,九哥早上起来去洼里看看玉米有没有被风刮倒,完事儿慢悠悠的踩着黄土泥返回来。
进村的丁字路边,一侧是打谷场,打谷场中间有一根低压电线杆,其中一根电线被风吹断后耷拉在麦秸垛上,九哥可能是出于职业操守的心理,怕来往的人那个不小心触电,准备把电线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大概九哥对于自己的职业技术太过自信,忽略了低压电弧的威力,在这个寂静的清晨,死神牢牢的扼住了九哥的喉咙,再也没有松手。
事后我一个堂哥说,早上正在喝汤(豫西方言,特指早餐或者晚餐),忽然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凄厉惨叫,堂哥饭碗一丢,越墙而出,看到九哥手里拉着电线衣袖已经被电弧起火点燃,情理之中的堂哥在距离不远的地方被电场强度通量辐射麻倒,幸亏反应快,反身回去找一根干燥长木杆,把九哥手里的电线打掉。九哥一只手的手指被电弧全部烧断,面目狰狞扭曲,已魂飞天外。
事后,单位矿上以非工作时间事故拒绝承担相关责任,单位来人看了看,象征性的问一下事情经过,又象征性的给了三万块钱,至于丧葬费、职工死亡补贴一概不提,九哥一死,价值三万块钱。
可怜的九嫂,面临家庭的巨变本来性格就恬静绵软,平时被呵护备至,九哥罹难已经让她乱了方寸,既不会据理力争,又不会撒泼无赖,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画上句号。人世间的一切九哥终于可以撒手不管,时间对于九哥而言,定格在199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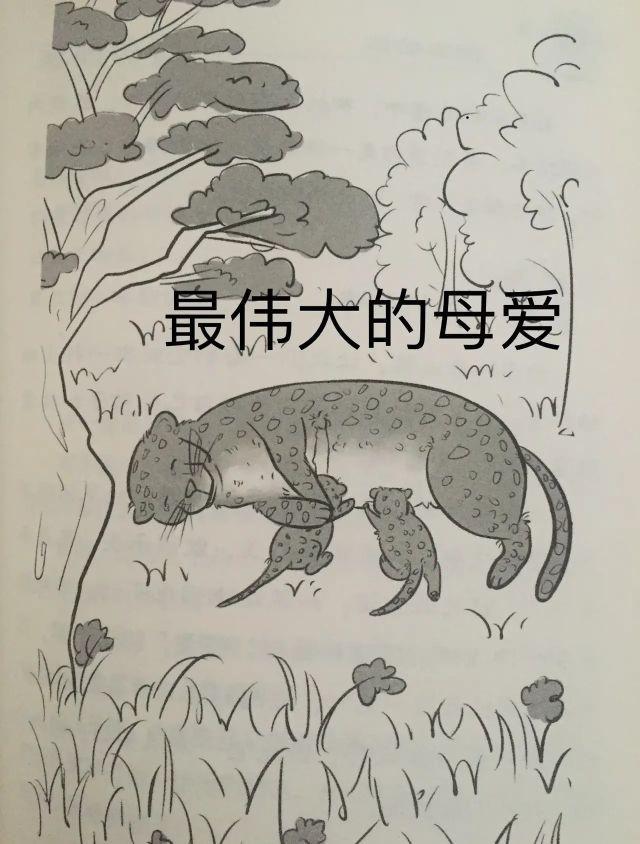
九哥终于像风一样的吹过,
但是日子还要继续啊。
九哥的风没有吹到别人,倒是把九嫂的生活吹的波澜横生。
后来家族里五嫂牵线搭桥,九嫂改嫁我们同村的一个侄子,(豫西风俗,同姓出了五服可以有婚姻关系,其他地方不详)对方是一个老鳏夫,不过为人口碑非常好,红白大事、邻里纠纷经常有这个鳏夫的身影出现,私下里这种人统称为事儿上人。在村里有相当的威望,颇有长者风范。
起初九嫂相当抵触这门半路婚姻,不过看看正在读书的两个未成年女儿,就再也没有拒绝的硬刚和倔强坚持的底气。老鳏夫也有子女,两个残破的家庭组合后,相处也颇为融洽。一时间村里人都以为九嫂和两个女儿幸福的生活即将到来,命运关上了一扇门,总要打开一扇窗吧。
写到这里笔者的内心一度非常的纠结。
都说幸福总是环环相扣,我觉得不幸也是。
婚后两年倒也相安无事,九哥的两个女儿也在继续读书,大女儿已经初中快毕业,学习非常优异,小女儿也小学毕业了。生活的一切似乎归于平静,时间总会让有些东西慢慢的淡化,淡到无人念及,或者刻意的遗忘。
小时候看电影或者戏剧,看到一团欢天喜地,或者艳阳高照,我的心就揪成一团,因为下一个画面就是生离死别,亦或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喜剧就是把血淋淋的悲惨掩盖在无厘头的搞笑方式里,在星爷经典刻意的周氏笑声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生活困境和人间辛酸。

我觉得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只是习惯选择了对别人不幸的钝感,对别人生命中飓风吹过的疼痛和绝望选择了视而不见的麻木和漠然。
后来的九嫂喜欢上了基督,人到中年的九嫂几乎把全部对九哥的怀念放在了高耸入云的尖顶教堂里。我想,如果不是对两个女儿的牵挂,大概率教会的唱诗班会是九嫂最幸福快乐的地方。在悠扬的风琴声中和虔诚的咏颂歌声里,面无血色的九嫂神情愉悦而平静,眼神里充满了对天国的向阳和期待。似乎在耶和华爱的沐浴里,九嫂完成了对自己的宽恕和原谅。
1994年的秋天,九嫂在镇上的十字路口不幸遭遇车祸,九嫂的名字叫幸。真是讽刺啊。
1996年的秋天,我从打工的新疆再次回到河南,和九哥的大女儿同在洛南一个私人的钢铁加工厂里打工。这个小小的加工厂里干活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乡邻,九哥的大女儿负责我们的餐饮,其实农民工的饭食相对比较简单,煮熟即可,咸淡不论,对厨艺零基础的女孩倒也没什么难度。当然了,也可以理解为乡邻之间对命运多舛的九哥后人,再次以这种微不足道的朴实方式施以援手。
1996年九哥的大女儿已经18岁了,继父在九嫂出车祸后迅速和两个孩子撇清关系,九嫂的身后事和事故理赔全由九哥的连襟处理,介于中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利益纠纷,外人实在难以了解真实的情况。
事实上两个女孩的窘境是,在姨夫的家里没法居住,在村里居住夜里又会被邻村的小青年骚扰,敲门、往院里扔石头,可怜无人依靠的两个女孩提心吊胆夜不安寝。
(限于字数,更限于工作时间原因,暂时更新到这里,友友们感兴趣可以关注更新进度。)
-

- 东北虎被神秘猛兽吃得尸骨无存,战斗民族俄罗斯称它为“撒旦”
-
2025-04-24 22:40:34
-

- 张永兴:东北抗日红色特工,传递出日寇防线情报,最后用枪声预警
-
2025-04-24 22:38:20
-

- 小说推荐:10本近期完结高分小甜文,男主超宠女主,撩的没心没肺
-
2025-04-24 22:36:06
-

- 东呈旗下精途酒店品牌介绍
-
2025-04-24 22:33:52
-

- 格斗术专家—动作明星斯科特·阿金斯
-
2025-04-24 22:31:37
-

- 「汝州女儿城」“最美非遗传承人”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
2025-04-24 22:29:23
-

- 中国四大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
2025-04-24 22:27:09
-

- 海韵教育丨中小学家长必读:什么是指标生?
-
2025-04-24 16:06:24
-

- “塔希提球王”宫磊——唯一被提名“世界足球先生”的中国球员
-
2025-04-24 16:04:10
-

- 飞鱼服,绣春刀,带你深入了解明朝神秘机构:锦衣卫
-
2025-04-24 16:01:56
-

- 同床共枕并生一子,妻子竟是男人?时佩璞瞒天过海隐藏男儿身20年
-
2025-04-24 15:59:42
-

- 扒一扒韩国顶级化妆品牌:爱茉莉旗下的雪花秀各个系列 !
-
2025-04-24 15:57:27
-

- 80年代最红主持人刘璐,晚年患上精神疾病,如今70岁的她过得怎样
-
2025-04-24 15:55:13
-

- 唐剑:我和法院的倾城时光
-
2025-04-24 15:52:59
-

- 印度花220亿卢布建造大坝,号称超越三峡,为何开闸不到一天崩塌
-
2025-04-24 15:50:44
-

- 湖南怀化通道万佛山,旅游度假好去处,著名观赏爬山风景区
-
2025-04-24 15:48:30
-
- 《向往的生活3》录制地曝光!红石林、层叠苗寨...美景不输蘑菇屋!
-
2025-04-24 15:46:16
-

- 足彩14场分析:布莱顿主胜 拜仁客胜
-
2025-04-24 15:44:02
-

- 解析罗曼蒂克消亡史波澜跌宕的剧情
-
2025-04-24 15:41:47
-

- 军队文职人员休假政策,干货来了!
-
2025-04-24 15:39:33



 一条烟不开封可以放多久?
一条烟不开封可以放多久? 彭冠英张含韵被曝结婚:低调的幸福爱情婚姻,或许与她的经历有关
彭冠英张含韵被曝结婚:低调的幸福爱情婚姻,或许与她的经历有关 王治郅的妻子周蕾,身材高挑 才貌双全 照片欣赏
王治郅的妻子周蕾,身材高挑 才貌双全 照片欣赏 范冰冰不雅图片 范爷大尺度裸身戏遭曝光
范冰冰不雅图片 范爷大尺度裸身戏遭曝光 扎西顿珠视为信仰的宗庸卓玛与平凡丈夫的爱情,七年卧床不离不弃
扎西顿珠视为信仰的宗庸卓玛与平凡丈夫的爱情,七年卧床不离不弃 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简历
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简历